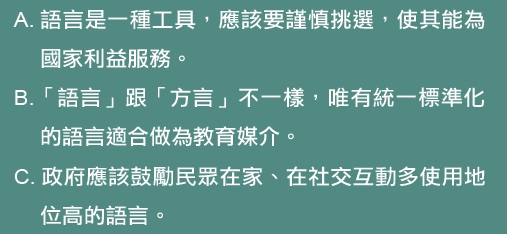L. Quentin Dixon
擔任於美國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教育與人類發展學院之教學、學習及文化部副教授,擁有美國布林茅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人類學學士學位, 以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人類發展及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專長為語言及文學。Dr. Dixon 的研究興趣聚焦在年輕英語學習者的語言和識字發展,也關注於為英語學習者創造有效的教育計畫,並採用嚴謹的定量研究方法,來評估計畫是否對英語學習者有所幫助。在取得研究學位前,Dr. Dixon在美國西雅圖附近的華盛頓州公立小學教授第二語言。
摘要
從國際評比研究來看新加坡的官方雙語教育政策──大多數的新加坡學童並不是用母語為媒介來受教育,而他們所謂的「母語」只是學校一門課而已──這已在人口和高等學業成績方面產生劇烈的語言改變,而根據現行的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理論,預測這樣的政策勢必會以失敗收場。本論文檢視該國語言政策背後有關語言規劃以及第二語言習得的種種假設,也檢視這些假設跟當前相關理論的關聯,此外,本文也探討新加坡的例子能否佐證或挑戰當前這些理論。
關鍵字
・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
・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
・語言教育政策(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新加坡(Singapore)
被讚譽為教育成功典範的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多語島國,官方採行雙語教育政策,從學生入學開始,英語即為所有科目的授課媒介,只是學生仍須修習一門官方「母語」(註1),以單一科目習之。由於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在國際評比中以優異成績獲得認可,例如第三屆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研究(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以及閱讀識字研究(Progress in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PIRLS)(PIRLS; Elley, 1992; Martin et al., 1999; Mullis et al., 1999)中所獲得的評比成果,使得這個城邦的教育制度成為政府語言規劃的一個絕佳範例(請見Dixon 2005,有更詳盡探討的實證資料)。雖然在最終的學術成績上表現優異,但是新加坡的語言教育政策所根據的諸多假設, 並未完全獲得當前語言規劃理論、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佐證。
背景:新加坡的語言、經濟、社會脈絡
新加坡於1965年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之後,語言規劃就一直是教育政策、社會政策一個重要角色。新加坡由三個主要族群組成,組成比例分別為:華人佔77%,馬來人佔14%,印度人佔8% (新加坡統計局,2001),這樣的比例從1900 年左右一直穩定維持至今(Chua,1964)。1965 年取得獨立之後,新加坡選擇成為多語城邦,明訂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Mandarin, 普通話)、馬來語、淡米爾語(Tamil)(Pakir, 2000)。其中,英語被提升為新加坡各族群溝通的「實際使用語言」(working language),其他三種官方語言則被視為各主要族群的「母語」(Rubdy,2001)。儘管獨立後,絕大多數新加坡人在家並不是說英語,這似乎意味他們在家使用的是所謂的「母語」。但事實上,新加坡華人在家中幾乎不說華語,他們說的是各種不同的中國語言(稱為「方言」),像是福建話、廣東話或潮州話(Afendras and Kuo,1980)。此外,在1957 年,新加坡的印度人中也只有60% 在家裡講淡米爾語,其餘印度人則是講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泰盧固語(Telugu)、印地語(Hindi)、旁遮普語(Punjabi)、孟加拉語(Bengali)、烏爾都語(Urdu)、古吉拉特語(Gujarati)(Afendras and Kuo)。在新加坡,只有馬來人在家裡是使用官方選定的母語。檢視新加坡獨立時的經濟、社會、政治情況,會有助於了解為何是這幾種語言獲選為官方語言。
1965 年的經濟、社會、政治情況
1959年,新加坡從英國手中取得自治地位,準備跟馬來西亞合併;1963年新馬正式合併,可是政治上的分歧,導致新加坡於1965年脫離聯邦(Tan,1997a)。只有637.5平方公里(CIA, 2001)的新加坡好不容易贏來了獨立,但周圍大上許多的好戰鄰國,也為新加坡能否持續獨立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當時世界各國政治領袖與觀察家都不看好新加坡的未來(Kissinger,2000)。新加坡於1959 年準備自治時, 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只相當於400美元(Lee, 2000)。當時,新加坡的經濟仰賴貿易,大多為進口、加工、再出口到他國的轉口貿易(新加坡政府,1965)。印尼當時是新加坡第二大貿易夥伴,由於印尼反對馬來西亞聯邦成形,於是在1963年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實施貿易禁運,另一方面,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後,馬來西亞也想繞過新加坡港口(LePoer,1991),因此, 新加坡的轉口貿易減少了23%(新加坡政府,1966),同時,國內失業率高達7.4%,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人(新加坡政府,1966)。
在1965年當時,新加坡有超過半數人口是20歲以下的年輕人,因此年輕人失業的問題很嚴重, 光是要讓失業率不再惡化,每年至少就得創造3% 的就業率。本身沒有天然資源,再加上轉口貿易遭到鄰國破壞,使得新加坡亟需快速轉變它的經濟型態(Yip et al.,1997)。於是,新加坡擴大公路、電、水、港口設施、工業設施等必要的基礎建設,努力加速工業化,並且鼓勵新的製造商進駐(新加坡政府,1966)。
新加坡的社會情況似乎也同樣不穩定。英國政府一向對三大主要族群採取分治策略,在地理上和族群上都是如此(Kwan-Terry,2000)。1964年,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邊為了合併後新設法律的議題而發生爭端的期間,新加坡的馬來人和華人也爆發了種族暴動(Tan,1997b)。一個彈丸之地、倔強又飽受貧窮與失業所苦的國度,如何在充滿敵意的鄰國環伺之下生存?這個脆弱、多語、充滿種族隔閡的城邦又該如何處理敏感的語言問題?
註1:由於這些所謂的「母語」並不一定是學生在家裡學到的語言,因此本論文特別加上引號,以示這是新加坡特別的情況。
從自治時期到1990年間始終擔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新加坡政府,2006b),這時候高舉經濟大旗,推動了他所屬的政黨選擇以英語做為新加坡獨立後的官方語言,並且,政府也鼓勵民眾以英語做為跨族群溝通的語言(Lee, 2000)。不過,李光耀也認知到,不能只採用前殖民政權的語言做為官方語言,於是另外也選擇了三大族群的主要語言為官方語言。
針對華人,他們選擇了華語作為官方語言,因為早在20世紀初學校引進華語授課以來,華語已經在受過教育的華人心中取得一定的地位;淡米爾語則成為了新加坡印度人的官方語言,因為它是最多印度人使用的語言,也是印度人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育中使用最悠久的語言;至於馬來人族群,則是毫無懸念地選擇了馬來語作為官方語言。
作為這個未成氣候的新國家的總理,雖然李光耀認為唯有精通英語才能為新加坡帶來國際貿易與投資,也才能通往西方科學與技術領域。然而李光耀也很清楚,基於政治因素,他不能強迫所有人都進入以英語授課的學校,也不能將英語地位凌駕於三大族群的「母語」之上(Lee, 2000),於是他轉而改採一項政策,允許父母自由選擇子女以何種語言接受教育,同時強迫要求非英語授課學校的學生必須學英語,而英語授課學校的學生則必須從三大「母語」之中擇一學習。
新加坡的語言教育政策
1966年,父母可以替子女挑選以哪一種官方語言接受教育(英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四擇一),不過學生必須從另外三種官方語言中挑一種語言學習。若是就讀非英語授課的學校, 就一律得學英語(Yip et al.,1990)。接著,政府要求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必須要用英語教授數學和科學。到了1979年,在「隱形的語言規劃」(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Pakir,1997) 之下,父母不再讓子女就讀以馬來語和淡米爾語授課的學校,而華語授課學校的入學率也下滑到只剩全體入學新生的10%左右(Yip et al., 1990)。
接著,新加坡政府採取雙語教育,也就是目前實施的政策,只是有些許修正:學生一律以英語為授課媒介來學習各個科目,同時也必須學自己的官方「母語」,熟練程度必須達到可稱為「第二語言」的程度。也就是說,華人必須學華語,馬來人必須學馬來語,而講達羅毗荼語(Dravidian-speaking, 即Tamil、Malayalam) 的印度人則是學淡米爾語。
如果不是講達羅毗荼語的印度人,則另外提供印地語(Hindi)、旁遮普語(Punjabi)、孟加拉語(Bengali)、烏都語(Urdu)、古吉拉特語(Gujarati)這幾種「母語」,讓學生透過「社區經營的週末課程」來學習(Saravanan,1999)。自1990年代以來,政府雖然有提供以上述能見度較低語言來進行的國家考試,但一直到2008年才給予官方資金,補助這些語言的教學(教育部,2007b)。如今,已有大約95% 的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來學習高階「母語」課程(教育部,2006),此外,從2008年也開始廢除學生分流制度,代之以「科目分班」制度(教育部, 2004),新制度依據四個科目的成績來分班(四科目為英語、「母語」、數學、科學),讓成績較差學生可按照自己各科的程度獲得適當安排。
新加坡學生念完小學六年後,必須參加「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簡稱PSLE)。以往,離校考試的成績會決定學生接下來就讀何種課程,也會隨之決定他們接受不同程度的「母語」學習。在2006 年之前, PSLE 成績前10% 的同學會編入「特優流」(Special stream),可修習高階「母語」課程;而大約50% 的學生則編入「快捷流」(Express stream),修習「第二語言」程度的「母語」課程; 至於其他40%的學生,則編入「普通流」(Normal stream),其下再分「學術組」(Academic)與「工藝組」(Technical),且「普通流」學生修習的「母語」課程程度也更低。
慢慢的,可學習高階「母語」課程的學生範圍逐漸擴大,只要是PSLE成績前11%到30%、「母語」考試成績同樣也很好的學生都可修習;最後,教育部宣布,任何學生想修習高階「母語」課程都可以,「只要他們被評定母語能力(MTL; Mother Tongue Language)優秀, 並且有能力在不影響其他科目成績的情況下修習高階母語(HMTL;Higher Mother Tongue Language)」(教育部,2007c)。
新加坡當地大學的入學資格有一部分也由「母語」考試成績決定。新加坡三所大學都要求國內申請人提供「母語」考試成績,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南洋理工大學(NTU)還會額外給「母語分數較高」的申請學生加分,不過,如果先去念理工學院且成績優異者,可以不理會這項要求。
新加坡自獨立以來一直是單一政黨執政,也就是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因此語言規劃和教育政策得以延續。人民行動黨用「務實」來形容他們的治國方式(Wee,2002),他們會隨著情況改變來調整政策。在制定、辯護語言教育政策時,新加坡政府仰賴的是許許多多的假設,其中有一些假設顯而易見,但有更多是諱莫如深,以下就根據當前的相關理論一一檢視這些假設。
新加坡政策背後的語言規劃假設
很有趣的是,這些假設混雜了語言規劃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st)、規範性、(prescriptive)、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 等傾向。在假設A,新加坡政府採取工具主義的觀點,認為語言是一種工具,應該要為國家利益服務(Tauli, 1968)。此外,新加坡政府也強烈採取規範性觀點,認為不論是文字或口語形式,唯有適合用於教育才可稱為「語言」(假設B)。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在推廣政策時,似乎又常常順應或鼓勵普遍形成的社會語言學趨勢(假設A、B、C)。
工具主義者把語言視為一種工具,認為語言或語言特徵是可以客觀評量的,然後再以此來判定哪一種語言適合用於哪一種功能(Appel and Muysken,1987)。工具主義者並未「想當然地認為」現存的文學語言(literary language)最適合用於教育,因為文學語言往往依循古體(archaic form)或語域(register)(Appel and Muysken,1987)。工具主義者認為文字附屬於口語之下,他們極力主張使用最簡單、最有效率的語言形式,不論是「方言」或比較德高望重的語言形式皆可(Tauli,1968)。
現存的文學語言雖然地位較高,但往往是缺乏效率的古體,工具主義者認為應該根據日常白話發展出一種比較簡單、比較有效率的標準化書寫文字,就算日常白話的地位較低也無所謂(Tauli, 1968)。雖然工具主義者主張這種理性、客觀的語言規劃方式,但是他們也承認,政治現實可能會阻礙地位低下語言的接受度,若碰到這種情況,建議從改革文學語言著手,將文學語言更拉近白話。
由此看來,新加坡官員走的是工具主義路線,他們先衡量新加坡在獨立之初使用的各主要語言,然後決定唯有英語能促進新加坡經濟的工業化、現代化(Yip et al.,1990)。可是,新加坡的此一決定,並非是基於英語的語言特徵,例如英語比其他語言更簡單、更清楚之類,而是基於英語可帶來的經濟利益,因為英語是跨國企業、科學與科技創新重鎮所使用的語言(Lee, 2000)。
雖然採取工具主義觀點,但新加坡政府同時也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權衡社會情況,採取分階段方式,逐步落實其語言教育政策,這一點從政策主要建置者李光耀總理以下談話可略知一二:
當各個種族都強烈地、熱情地投入他們的「母語」,在這種時候斷然宣布所有人民一律要學習英語,必然是災難一場……,我不想開啟語言爭端,於是在英語學校引進三種母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的教學,贏得家長的讚許。為求平衡,我也在華語學校、馬來語學校、淡米爾語學校引進英語教學,馬來人和印度人家長對此表示歡迎,但卻有越來越多人寧可把子女送進英語學校。死忠堅持採用華語教育的人並不樂見英語成為共通的「實際使用語言」(working language),他們在華文報紙上表達不滿(Lee, 2000,p. 146)。
儘管有些華人不樂見學校和社會朝向更多的英語發展,但是同一時間,絕大多數華人父母卻選擇讓子女就讀英語授課學校,選擇英語教育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多(Chiew,1980)。因此,新加坡政府便順應這股社會語言學趨勢(亦即父母將子女送進英語學校的趨勢),而不是試圖對抗此一趨勢或貿然加速趨勢。
由此來看,新加坡政府在權衡每一種語言的現況時,似乎採取了社會語言學的觀點(Appel and Muysken,1987),但同時又排除了社會語言學的「所有語言皆平等」的主張(Eastman,1983)。
社會語言學家主張,沒有任何方言或語言不適合授課,因為所有語言天生平等(Appel and Muysken,1987)。某種語言或許會因為欠缺合格師資、課本或教材而產生教學實務上的障礙,但並不代表該語言或方言本身就次於其他在教學實務上萬事具備的語言。
然而,新加坡政府同時也援引「規範性」傾向,對於人民在家、在學校應使用何種語言有明確規範(假設B 和C)。在英語方面,新加坡政府發起「講正確英語運動」,積極鼓勵人民使用「標準」英語(英式英語),取代當地人常講的在地化英語,也就是所謂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Chua,2004)。此外,新加坡政府也推出「講華語運動」,大力推廣講華語、不講方言(Kuo, 1984;Newman,1988;Chua,2004)。不論是講正確英語運動或是講華語運動,新加坡政府只認可使用於教育的語言。
規範語言學(prescriptive linguistics)尋求一種「理想的」或「純粹的」語言,供政府和全國語言研究院去定義、捍衛(Eastman,1983),規範語言學家贊成鼓勵人民使用地位高的語言。而社會語言學家的主張則是,文字勢必比口語更傳統守舊,因此「正確」的口語說法不只一種,他們指出,不管在哪一個社會,人民會因不同的目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各種不同語域(registers)(Eastman,1983),試圖限制人民只能使用一種標準用法,這樣的做法絕不可能成功,因為口語是一個動態的(dynamic)、活的系統,會一再歷經協商妥協、變化。
新加坡目前使用的各種不同英語語域都記錄在冊(Pakir,1999),可佐證社會語言學家的這套理論。就新加坡的例子來說,新加坡人越來越常使用Singlish 便是社會語言學趨勢,而政府積極試圖扭轉此一趨勢,一再強調標準英語在經濟上的實用性勝過Singlish(請見Lui,2006)。
就中文而言,只有華語被新加坡政府視為「語言」,而早在獨立之前,就有更多新加坡人聽得懂的其他中國語言(例如: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被視為「方言」,不配用於教育或其他官方領域(Pakir,1997)。在這個政策下,孩童的語言來源被視而不見。對絕大多數華人來說,一開始進入學校時會因為家庭的文化傳承而講某一種中國方言,但方言卻被視為是學習華語和英語的障礙(Lee,2000)。
然而根據Newman(1988)的報告,透過援引兩種語言的相似之處,福建話流利的人有九成的機率可猜出任一個字的華語發音,可是這種學習華語的潛在優勢卻遭到新加坡政府捨棄,並轉而要求所有華人在家、跟其他華人溝通都使用華語。
20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正熾,伴隨這股熱情,新加坡早在獨立之前就已經開始這種犧牲方言、獨尊華語的政策(Ang,1999),因此新加坡華人似乎很接受這項政策,也把華語視為唯一適用於中文教育的語言。社會語言學家雖然不認為華語在教育方面優於其他中國語言,但也預測這樣的語言政策有較高的成功機會,因為推廣地位低下語言的政策往往會遭到民眾抗拒(Haugen,1971)。
同樣的,一開始,新加坡捨棄印度族群實際使用的口語淡米爾語,反而選擇古典淡米爾語來推廣,並明訂為學校使用的語言,不過這項政策近來已改弦易轍,顯然是認知到學生學習古典淡米爾語有困難,口語淡米爾語於是成為官方採用的授課語言(教育部,2007a)。
此外,最初要求印度族裔學生一律必修淡米爾語的政策也鬆綁,改為讓學生可在校外學習他們家裡實際使用的語言,以取得「母語」必修學分。近來,政府也開始提供資金,協助這些能見度較低印度語言的教學(教育部,2007b)。這些攸關印度族群的政策轉彎,顯示有稍微偏離上述假設的跡象。
也就是說,站在工具主義的觀點,無論是否贊同華語在教育上優於「方言」,都必須取決於華語文字是否在經濟、效率、清楚三大標準勝過其他方言(Tauli, 1968),而不是取決於華語在中文教育的既有地位。工具主義者會贊同新加坡政府捨古典淡米爾語、採用口語淡米爾語做為授課語言,因為白話能讓多數人了解,表達方式很可能也比較簡單、有效率。
不過,社會語言學家可能會指出越來越多印度家庭在家說英語的趨勢,以此證明,就算改用口語淡米爾語授課,可能也只是減緩印度族群改用英語的趨勢,無法翻轉趨勢。似乎只有馬來語不管從工具主義或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都是適當的選擇,因為馬來人在家使用的語言跟課堂上使用的語言是一致的。不過,就連馬來語也漸漸失守,逐漸敗給英語,特別是社經地位高(SES) 的家庭(Aman,2007 ISB61 報告)。
新加坡英語教育政策的成功(註2),或許可歸因於英語的地位高。新加坡政府一開始並未強迫規定使用某一特定語言授課,而是提供選擇給家長,
結果家長大多為子女選擇英語教育,然後政府再順應這股趨勢,讓社會語言學主導政策的演變。
不過,現在有越來越多孩童把Singlish 當成第一語言或初期第二語言來學習,政府推廣標準英語的努力,不知能否成功遏止這股朝Singlish 走去的社會語言學趨勢(Stroud and Wee, 2007)。
把華語提升為地位高的語言,已經使得華人在家裡以及與人互動都大幅捨棄方言、改用華語(Rubdy,2001),只不過有些研究指出,他們的華語程度(特別是寫作方面)並不是全部都很高(Hsui,1996;Cheng,1997)。
不過,提倡古典淡米爾語做為印度族裔的官方語言卻成效不彰,導致後來政策改弦易轍,改採口語淡米爾語授課。一份針對淡米爾語教師的調查指出,標準口語淡米爾語(說淡米爾語的高教育程度人士發展而成的語言)或許會被廣為接受為授課語言(Saravanan et al.,2007)。這項政策能不能讓淡米爾語課堂的學生有更好表現, 仍有待時間證明,或許會扭轉印度家庭走向英語的趨勢也說不定。
新加坡政策背後隱含的第二語言習得假設
越早開始學習第二語言,
越能精通該語言
新加坡要求學生從一開始進入正規學校就強調第二語言(L2),也就是英語,此一政策顯然是基於一種想法:孩童越早開始學習英語,可以學得越好。當時的總理李光耀極力主張父母「盡早」教子女英語(Lee,1982,p. 5)。後來, 1990 到2004 年擔任總理的吳作棟(新加坡政府, 2006a),在一場演說當中發起了「講正確英語運動」,他的說法如下:
學習正確英語最好從小開始,等到年紀大了才學比較困難,不過還是做得到,也值得付出心血去做(Goh,2000)。
「越早開始學習第二語言,越有可能精通該語言」是個普遍被接受的假設(Marinova-Todd et al.,2000)。這個假設正是第二語言研究者爭論不休的「關鍵期假說」(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或「敏感期假說」(sensitive period hypothesis) 的核心。根據關鍵期假說,語言學習有個「關鍵期」( 或說「敏感期」),通常在青春期之前,在關鍵期過後,學習者就算仍有可能把第二語言學到母語人士一般的水準,但很困難。雖然有很多研究證實,越早學習語言有發音上的優勢(Oyama,1976/1982),或許在文法上也有,但是年紀是否也會決定第二語言其他方面的學習成效,目前取得的證據仍莫衷一是(Bialystok and Hakuta,1999;Marinova-Todd et al.,2000;Garcia Mayo and Garcia Lecumberri,2003)。
由於一直觀察到有成人學習第二語言(L2)學到非常精通的程度(Birdsong,1992;Marinova- Todd et al.,2000),因此採嚴格生物學觀點的關鍵期假說顯然站不住腳。不過,仍有許多研究證明,如果是移民來到移居地學習新語言,較年輕學習者的確有明顯的優勢(Johnson and Newport,1989/1995)。但是,就孩童而言,如果只是把英語當成在學校學習的一門外語課,研究顯示,在上課時數都一樣的情況下,較晚開始學習者有明顯的優勢(Garcia Mayo and Garcia Lecumberri,2003)。
新加坡的情況比較類似後者,也就是英語只是在學校學習的外語課程,因為絕大多數新加坡人民的母語並非英語,比起移居到美加等單一語言國家的少數移民學生,新加坡學生在家、在街頭接觸到的英語比較少。雖然環境不一樣,不過, 雙語城市蒙特婁位於加拿大的法語省份魁北克,這座城市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能提供一個對照的樣本,可跟住在多語環境的新加坡中,英語不是母語的孩童或雙語孩童做一對照。
比較蒙特婁以英語為母語的孩童早進入與晚進入法語課程的不同,可看出到了十年級、十一年級,這些學生接觸法語的量雖然相差很大,在聽、讀、寫、說的表現卻都一樣(Swain and Lapkin,1982)。很早進入全法語課程的學生,在四到十一年級接觸法語的量減少為四成;晚進入法語課程的學生在七年級之前極少接觸法語(一天約半小時),到了七、八年級則有八成以上的授課是以法語進行。在這個例子當中,起步早的學生雖然累積的法語授課時數比較多,但他們的表現並沒有比晚起步者好。
註2:新加坡英語教育政策的成功並非是全面一致性。以國際標準來看,新加坡學生平均而言在教育上的表現極為優秀,不過,不同族群的學業成績有落差,很可能是因為社經環境的差異(Stroud and Wee,( 參考P.52)2007)。
檢視了關鍵期假說相關文獻之後,Marinova- Todd 等人(2000)承認,整體來看,較年輕學習者的表現的確優於較年長學習者,不過,因為仍存在著年長學習者能夠非常精通L2的情況,於是引人深思,是什麼因素使得年長學習者也能精通L2?這些研究結果並未斷言較早開始學L2一定具有絕對的優勢,畢竟有些較年長的學習者也可以達到精通程度,但問題是,為什麼一般來說較年輕學習者比年長者容易達到精通程度?是不是可以設計出一套課程來改善年長者的最終學習成效?
有些L2研究人員認為,孩童和成人接收到的語言輸入(input)不同,於是造成L2程度的不同。贊同這種「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的人認為,語言輸入的品質是L2 最終學習成果最重要的因素,跟學習者的年齡無關(Krashen, 1982,1985)。根據這樣的理論,任何年齡開始學習L2 都可以,而老師的角色就是提供該有的語言輸入,以幫助學生(不管年輕或年老)達到精通程度。
新加坡政策背後的假設很清楚:如果越早學越好,那麼就應該在新加坡正規教育年齡一開始(或之前)就提供英語授課。可是,如果考量到輸入品質以及加拿大那個時數較少但成效較佳的例子,新加坡審慎的政策擬定者可能就會延後推出英語課程,以便把英語能力最好的師資集中用於較年長的學習者身上。
新加坡讓學童在他們年齡很小時就以英語授課的政策獲得的整體成功,佐證了「越早開始越好」假說,不過,由於新加坡並沒有實驗在不同年齡推行英語授課的成效,並以此來斷定最佳的推行年齡,因此,其英語教育的成功不能導因於學童早齡期的英語推行。
發展家庭語言(home language),
對增進英語學業成績沒有幫助
李光耀認為,要取得優異的英語成績,就應該多使用英語。他提出相關資料指出,「在家越常使用英語,EL1(English studied at a “first language”, 把英語當成第一語言來學習)的成績越好」,力勸馬來人父母在家多講英語:
父母必須做個取捨,是否要為了在家跟子女講馬來語(也就是母語)的便利,而犧牲子女的EL1成績。如果希望子女在EL1有優異成績,子女在家除了講馬來語之外也必須講英語(Lee, 1982,p. 5)。
隨著新加坡家用語言從「母語」(以及其他語言)逐漸改為英語,政府的政策重心也隨之改變,從推廣在家講英語轉為推廣在家講「正確」或「標準」英語,以取代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
如今,一年級學生已有二分之一在家以講英語為主,不過,我們了解到,很多新加坡人並不知道他們講的不是標準英語,也因而影響到子女學到的英語。父母是非常重要的模範,尤其在孩童的發展初期,因此,我要鼓勵家長閱讀優良書籍給子女聽,以便子女能培養出辨別正確英語的耳朵。如果家長不習慣講英語,也可以跟子女講母語,以培養子女用母語溝通的能力(Lui,2006,p. 3)。
以上談話雖然提到在家使用「母語」,但並未提到培養「母語」有助於學習英語,而是把「在家說母語」描繪成有助於達到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第二語言目標,也就是精通「母語」。此一假說(發展家庭語言對增進英語學業成績沒有幫助) 跟「移轉假說」(transfer hypothesis)互相牴觸,移轉假說主張,學習者透過家庭語言學到的學術理論,可輕易移轉到L2,家庭語言若有高水準程度,則有助於孩童在L2達到高水準程度,反之亦然(Cummins 1979,1981,1991)。舉例來說, 透過某一種語言學到的概念,可輕易移轉到另一個語言,只要學習必要的新詞彙即可,此外,透過某一種語言學到的閱讀能力和其他各種後設認知能力(metacognitive skill),也可輕易地透過L2理解,只要有足夠的L2能力的話。
針對「家庭語言跟學校語言不一樣」這個問題,新加坡的解決方法是改變家庭語言,而不是在學校用家庭語言授課。雖然新加坡學生整體的教育成績很高(根據國際評比研究來看),但如果政府培養的是家庭語言(針對在學校學習兩種非家庭語言的學生)或以家庭語言為重心(針對現在只把家庭語言當成學校一門課來學習的學生),會不會讓新加坡的成績表現更好,不得而知。
投入越多時間學習某個語言,
會對該語言越精通
早在新加坡分別以四種語言來授課時,政府規定非英語授課學校一律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結果學生的英語程度並未達到高水準,政府因而要求所有學校一律以英語教授數學和科學(Yip et al.,1990)。儘管具指標意義的《教育部報告》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Goh,1979)引用證據指出,這個策略並未改善學生的英語程度,甚至反倒造成華語學校學生的科學成績下滑,可是,李光耀特別發表不同意見來回應這份報告:
你們團隊的結論是,雖然用英語來教授科學和數學,但是LET(Language Exposure Time;暴露於英語的時間)的增加並未改善華語學校的英語水平……,這個結論有違我自身的學習經驗,也違背我個人對學生的觀察。只要越常聽某一種語言,就會越容易聽懂,也越容易會講…… (Goh,1979,p. vi)。
李光耀堅信這個假設:學習語言的關鍵在於「投入時間的長短」,而不是「輸入品質(input quality)」。雖然有大量教育研究報告贊同「投入時間長短假說」適用於閱讀和其他科目(Snow,1990),但是花同樣時間在課堂學習L2 的學生卻有不同的精通程度,較年長學童較有優勢(Swain and Lapkin,1982;Harley, 1986),因此投入時間長短並不是第二語言習得唯一的因素,學習者的特質、語言輸入的種類,也必須考慮在內。
前面討論過,根據移轉假說,透過某一種語言學到的東西,可移轉到另一種語言(Cummins, 1991)。如果新加坡學生透過「母語」學到的概念、策略、技能等等,可輕易移轉到英語,那麼,投入於英語的時間長短,對整體成績的重要性就會降低,而英語的輸入品質反而應該納入衡量。「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強調應該提供高品質的語言輸入給學生(Krashen,1985)。
所謂高品質語言輸入,必須是學生容易理解的:也就是,可透過上下文、身體動作、實體物品、視覺輔助等方法來理解。
最理想的語言輸入是略高於他們現有的語言程度。傳統教學法如口述、依賴課本,未能提供容易理解的語言輸入,而容易理解的語言輸入卻是L2習得的關鍵(Krashen,1982)。
如果用第一語言授課,高中生或許能理解缺乏任何視覺輔助的講課內容,但是同樣的內容若以第二語言講授,對第二語言初學者來說勢必難以理解。因此,L2初學者很可能花了一整天聽取L2授課,卻只是「鴨子聽雷」,儘管他的投入時間很長,可以理解的語言輸入卻很少,很難期待他能學到多少L2;相反的,如果一個學生投入於L2的時間較少,但他是投入於某種適合年齡、他可理解的遊戲,他學到的L2可能就比較多。
另有一派人強調互動(interaction),一方面創造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同時也強化學習者的整體語言能力(Pica,1987;Pica et al.,1987)。透過確認是否聽懂、提出問題來釐清、指出不懂之處或確認聽懂之處,學習者可以促使對話者換個說法、改用另一個字彙、簡化或詳細說明某個陳述、補充資料,以此創造出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同樣的,對話者會提供重要的回饋(feedback)給學習者,用同樣的方法誘使學習者開口說明、釐清問題。對話者如果無法聽懂學習者的發言, 學習者就不得不換個說法、改用其他詞彙、詳細說明或簡化、補充資料,好讓自己的發言容易理解。同樣的,傳統課堂大多未提供諸如此類的互動機會。
Vigil和Oller(1976)利用一個模型來說明回饋會如何影響第二語言習得,他們假設,正面回饋和負面回饋都是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Long(1996)的「互動假說」強調對話的重要,特別是母語人士和L2學習者之間的對話,可刺激L2學習者習得目標語言。
根據Long的理論,在對話二人針對字義進行討論的過程中,L2學習者會注意到自己令人聽不懂(不標準)的說法,只要母語人透過「重述」(recast,也就是重新以標準說法糾正不標準的說法),L2學習者就有機會學到標準說法。「重述」是一種負面回饋,或許比「模仿」更有助於學習某些文法架構(Long et al.,1998)。互動回饋(interactional feedback),譬如針對字義進行討論、磋商、重述,或許對孩童學習第二語言更為重要(Mackey and Oliver,2002)。
Swain(1985,1995)則是強調「輸出」(output)對第二語言習得的重要,也就是「言語產出」(speech production)。語言輸出除了如上所述可提供回饋的機會,也可給學習者一個機會,去測試他們如何實際運作該語言,同時也可讓學習者不再只是專注於字義,而會在絞盡腦汁把字彙組合成正確、有意義的順序時,開始分析文法(Swain,1985),此外,還可讓學習者有機會「注意到」(Swain 1995,p. 126)他們不熟悉的文法形式,再者,老師也可以分派文法作業給學生,以揪出學生的文法問題(Swain, 1995)。
傳統課堂的授課方式通常沒有提供機會給學生進行語言產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以考試為目標,教學方法仍以傳統授課為主,要求使用英語的時間最大化,而不是高品質的語言教學。近年來新加坡嘗試改採比較偏向溝通式的教學方法,但因為學生仍必須準備升學考試而大打折扣(Cheah,1999)。新加坡學生在國際考試的表現非常好(Martin et al.,1999;Mullis et al.,1999,2003),但實際的英語口語能力可能不是那麼好。同樣的,由於欠缺對照組,也就是欠缺學習英語的時數較少、語言輸入品質較高、互動機會較多的學生當做對照組,很難判定新加坡強調「投入時間長短」的作法是否有道理。
有沒有能力學習一種以上語言,
跟整體學業成績有關
這是一種普遍的教育觀點,認為有些學生整體的學習能力比較強,有些比較弱,只有比較強的學生能夠應付兩種語言的高階學習。此一觀點似乎是遵循Charles Spearman等人的理論:人有一種一般性的整體本質,稱為智力,主掌一個人各種認知發展能力(Gardner,1983)。換句話說,數學、歷史、科學等等學得「很快」的學生,高階第二語言也會學得比較好,而在各學習科目學得「比較慢」的學生,就沒辦法應付兩種語言的高階學習。不過,Howard Gardner 等人提出另一種不同的觀點:智力並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東西,而是可以分割成好幾種不同智能(Gardner, 1983)。
根據Gardner 的理論,語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也就是學習、操控語言的能力)跟數學、音樂等等其他智能都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干,換句話說,數學優異的學生很可能在語言方面不是特別強,而語言優異的學生很可能在音樂方面不強。事實上,Pinker(1994)等研究人員就斷定,有一種天生的語言學習能力完全獨立於一般的智力之外,一般來說,學業成績優秀的學生不一定有能力將兩種語言學到精通,反過來說,一般學業成績不好的學生很可能有能力把兩種語言學好,只是他們的語言能力被成績不好的表象給掩蓋了。
在Harley和Wang(1997)的研究當中,他們用訪談來評量L2程度,結果,對很早就完全浸淫於L2課程的學生來說,L2程度跟智商無關;比起很早就有一部分浸淫於L2的學生,較晚浸淫於L2的學生較容易在L2取得好表現(Harley and Wang,1997)。這兩位作者提出,較年長學生的表現之所以比較優異,很可能跟教學方法有關。
新加坡的政策逐漸偏離此一假設。一開始,只有PSLE成績在前10%的學生有資格學習高階英語和「母語」,接著,這項條件開始鬆綁,允許PSLE分數在前11%到30%、「母語」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可學習高階「母語」。更晚近一點, 學校的作法更具彈性,只要學校認為不會干擾學生其他科目的成績,即使未達標準的學生也可學習高階「母語」(教育部,2007c)。
這樣的轉變似乎是因為認知到,各科目不優秀的學生也可能有能力學習兩種語言,不過,這項政策也暗示,成績未名列前30%但可學好兩種語言的學生是例外。「科目分班」制度也承認,學生在不同科目會有不同水準的成績表現,包括兩種語言也是,只不過一般還是假設,成績不好的學生沒有能力學習高階英語或「母語」。此外,學習外語(法語、德語、日語)仍然只限於PSLE成績前10%的學生,以及在語言方面有「特別天分」的學生(教育部,2007c)才有資格。
維繫族群語言,就可以維繫族群認同、「根」的意識以及文化價值
如上所述,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政策並不是為了讓老百姓普遍都具備高階的雙語能力、讀寫能力,此一特權只保留給成績最佳的學生,那麼,既然以英語為重,又為何要學習另一個語言,也就是所謂的「母語」呢?在談到華語教育時,李光耀寫道:
教導、學習華語的最大價值是:傳遞社會規範或道德行為規範……。
我們如果忽視了這點,而只把重點放在第二語言也要達到幾乎跟第一語言一樣的程度,那就會是個悲劇。應該讓馬來人子弟了解他們的諺語和民俗……至於印度人,羅摩耶那史詩(Ramayana)和摩訶般若多史詩(Mahabaratha)有極佳且取之不盡的故事…… 這些故事同時也傳遞了道德訊息,是文化精華。所有孩童在學校完成九年教育離開之前,自己文化的「軟體」必須已經灌入他的潛意識裡(Goh, 1979,p.v)。
早期,英語被視為科學與科技的語言,而「母語」則被指定為傳輸文化價值與規範的語言(Rubdy,2001)。根據Sapir-Whorf 假說, 一個人所講的語言會大致決定他抱持的想法(Kecskes and Papp,2000),Sapir-Whorf 假說可以用來佐證此一假設。
根據這個理論,孩童如果沒學「母語」,就無法學到家庭文化的傳統思維和價值,可是,這個理論遭到現代語言學家的駁斥,現在的語言學家認為任何概念都可以用任何一種語言來表達(Kecskes and Papp,2000),也就是說,不僅「母語」可以用來表達、傳遞傳統文化價值,英語也可以。
以心理學家Vygotsky 的理論為基礎的社會文化理論,對於語言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抱持的看法,並不像Sapir-Whorf 假說那麼決定論,但隱隱約約更贊同這個假設。根據這個理論,族語強調的是在文化上很重要的概念和範疇(Kecskes and Papp 2000),因此,學習一種語言可強化跟該語言相關的文化價值。
Fishman(1977)指出,語言是威力強大的族群符號,保留族語就可以保留族群界線。儘管如此,很難透過這些理論來判定,學習某種非母語的族語,是否就會達到傳遞文化傳統、價值、規範的功能。
回頭來看新加坡的例子,政府顯然不打算評斷「母語」是否成功扮演傳遞傳統價值的角色。「講華語運動」的成功與否,是根據華人有無在家裡、工作上、日常買賣改用華語來衡量,而不是根據有無維繫華人文化價值來衡量(Newman, 1988; Riney,1998)。
事實上,一直有一種主張認為,印度人雖然最普遍改用英語,但是他們對傳統價值的保存更勝於華人(Pakir,1993;Riney,1998),如果真是如此,真正決定傳統價值的保存或流失者,想必有語言之外的因素存在。
結論
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佐證工具論者和社會語言學家的語言規劃觀點。工具論者可以大力擁護「講華語運動」的成功(註3)(該運動推廣一種較簡單、標準化的語言,捨棄家庭方言),由於有越來越多華人把子女送進以英語為授課媒介的學校就讀,如果政府不強力要求學校設立華語課程,並且推廣學生在校外使用華語,華語可能會在新加坡滅絕。
不過,另一方面,社會語言學家也可以指出,華語在華人之間原本就有很高的地位,這才是此一政策成功的原因。此外,社會語言學家也可以以新加坡社會改用英語為例,證明政府只是鼓勵原有的社會文化趨勢(捨其他語言而選擇經濟上有利的英語教育),一直等到絕大多數的父母為子女選擇英語教育,新加坡政府才明訂以英語做為所有學校的授課語言。淡米爾語的例子則可佐證工具主義論者的主張:較簡單的語言比較適合用於教育,不論其地位高下。
究竟是新加坡政府採取的規範(prescriptive)立場是正確的,還是新加坡人會堅持使用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和方言,現在還不得而知。根據社會語言學家的主張,Singlish不可能遏止,如果把Singlish 當成一種非正式語域(register), 跟政府提倡的正式語域(也就是標準英語)並存,其實也無害。雖然新加坡政府推廣的「講華語運動」促使華人大幅從方言轉向華語,但是方言仍意外地持續用於某些領域。(see, e.g., Xu, 1999, p.196)。
新加坡的經驗並未解決L2習得領域任何持續不休的爭論,因為新加坡是遵照一套統一的政策,並沒有實驗早學英語跟晚學英語的差異,也沒有實驗接觸英語時間的多寡、多元教學法,不過,新加坡的例子當然還是證明了,一個國家可以成功實施一套廣泛的教育政策,在學生年紀很小的階段就開始以非母語授課,而且還不是很重視家庭語言的培養,而這套教育方法可以讓學生取得很優秀的學業成績(註4)。
至於這套方法能不能在其他環境大不相同的國家複製,則仍有爭論。新加坡是在一場重大危機中建國,或許因此導致人民比較容易接受政府的政策,特別是為了達到社會安定與經濟成長。
新加坡似乎已達成當初為語言教育政策設定的重大目標,不過,喪失豐富的語言多樣性、從多語轉變成雙語,或許也是始料未及的後果。Pakir(1993)提到,李光耀在1989年接受台灣記者訪問時說到,如果他有機會重新回到1965 年或1970年,他會保留華語小學,將華語小學的英語課程增加為第二語言的學習份量,同時鼓勵父母把小孩送進華語學校。然後,他會多給一年的時間(不是在小學就是在中學),協助一般學生做轉換,從以華語為第一語言轉換成以英語為第一語言來學習(Pakir,1993,p. 83)。
這套原則同樣會擴及以馬來語、淡米爾語授課的學校。如果這樣的話,英語成就會有什麼不同嗎?「母語」方面的成就呢?整體的教育成就呢?經濟成就呢?或者如同李光耀信守的理念,可保存傳統價值方面的成就呢?我們無法把時鐘撥回到從前去嘗試另一種情況,不過,其他國家若想複製新加坡的教育與經濟成果,就得從自身的情況來考慮這些問題。
如今,新加坡似乎走在一條單向道上,從多元的多語環境走向比較單一的雙語制度(英語和另一種官方語言)。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新加坡會變成更像只說英語的單一語言國家,而「母語」只淪為學校一門科目嗎?轉變成以英語為主的環境,會有礙將傳統價值傳遞給下一代嗎?未來幾十年,新加坡仍會是語言政策分析者、第二語言習得研究者一個很吸引人的研究素材。
註3:「講華語運動」是否成功,是根據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其他研究的紀錄,至於究竟達到多流利的程度則不論。
註4:學業成功與否的最佳衡量方法,當然是看這些學生完成學業後能否有成功的職業生涯,不過,這類最終結果的資料付之闕如,而國際測驗(例如TIMSS 和PIRLS) 可視為衡量學業成績的好方法,因為這些測驗並未特別針對哪個國家的課程來設計。
◎作者:L. Quentin Dixon
◎譯者:林錦慧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09
參考文獻
Afendras, E. A., & Kuo, E. C. Y. (Eds.). (1980).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g, B. C. (1999). The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In S. Gopinathan, A. Pakir, W. K. Ho, & V. Saravanan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pp. 333–352).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Appel, R., & Muysken, P. (1987).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Arnold.
Bialystok, E. (2001). Bilingualism in development: Language, literacy and cogn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alystok, E., & Hakuta, K. (1999). Confounded age: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age difference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 Birdsong (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pp. 161–181).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Birdsong, D. (1992). Ultimate attai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68, 706–755.
Cheah, Y. M. (1999). Acquiring English literacy in Singapore classrooms. In S. Gopinathan, A. Pakir, W. K. Ho, & V. Saravanan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pp. 333–352).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Cheng, N. L. (1997). Biliteracy in Singapore: A survey of the written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f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1), 115–128.
Chiew, S.-K. (1980). Bilingu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Singapore case study. In E. A. Afendras & E. C. Y. Kuo (Eds.),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pp. 233–253).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Chua, S. C. (1964).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Singapore: State of Singapore.
Chua, C. S. K. (2004). Singapore’s literacy policy and its conflicting ideologie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5(1), 64–76.
CIA. (2001). The world factbook 2001. CIA. Accessed December 4, 2001 from http://www.odci.gov/ cia/ publications/factbook/
Cummins, J. (1979).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childre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9(2), 222–251.
Cummins, J. (1981). The role of primary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educational success for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In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Ed.), Schooling and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pp. 3–49). Los Angeles, CA: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ummins, J. (1991). Interdependence of first- and second-language proficiency in bilingual children. In E. Bialystok (Ed.), Language processing in bilingual children (pp. 70–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L. Q. (2005).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An analysis of its sociohistorical roots and current academic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8(1), 25–47.
Eastman, C. M. (1983). Language planning: An introduction. San Francisco, CA: Chandler & Sharp.
Elley, W. B. (1992). How in the world do students read?: The IEA study of reading literacy. The Hague, Netherlands: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Fishman, J. A. (1977).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H. Giles (Ed.), ACLS-sponsored ‘‘ethnicity in eastern Europe’’ (pp. 15–5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arcia Mayo, M.d. P., & Garcia Lecumberri, M. L. (Eds.). (2003). Ag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Gardner, H.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oh, K. S. (1979).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pp. 113). Singapore: Education Study Team.
Goh, C. T. (2000).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Goh Chok Tong at the launch of the 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on Saturday, 29 April 2000, at the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TE) headquarters auditorium, Dover Drive, at 10:30 am. Accessed May 29, 2008 from http://stars.nhb.gov.sg/ stars/public/.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06a). Cabinet appointments: Mr GOH Chok Tong. Accessed May 29, 2008 from http://www.cabinet.gov.sg/CabinetAppointments/ Mr?GOH?Chok?Tong.htm.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06b). Cabinet appointments: Mr LEE Kuan Yew. Accessed May 29, 2008 from http://www.cabinet.gov.sg/CabinetAppointments/ Mr?LEE?Kuan?Yew.htm.
Harley, B. (1986). A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Harley, B., & Wang, W. (1997).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Where are we now? In A. M. B. de Groot & J. F. Kroll (Eds.), 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pp. 19–51).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augen, E. (1971). Instrumentalism in language planning. In J. Rubin & B. Jernudd (Eds.), Can language be planned? (pp. 281–292). Honolulu,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Hsui, V. Y. (1996). Bilingual but not biliterate: Case of a multilingual Asian society. Journal of Adolescent and Adult Literacy, 39(5), 410–414.
Johnson, J. S., & Newport, E. L. (1989/1995).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H. D. Brown & S. Gonzo (Eds.), Reading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75–115).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Kecskes, I., & Papp, T. (2000). Foreign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Kissinger, H. A. (2000). Foreword. In K. Y. Lee (Ed.),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pp. ix–xi).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Krashen, S.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 York: Pergamon.
Krashen, S.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Longman.
Kuo, E. C. Y. (1984). Mass media and language planning: Singapore’s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Spring), 24–35.
Kwan-Terry, A. (2000). Language shift, mother tongu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43, 85–106.
Lee, K. Y. (1982). Prime Minister’s add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gress of the 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Muslim Children (MENDAKI) at th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on 28 May 82. Accessed May 29, 2008 from http://stars.nhb.gov.sg/stars/ public/.
Lee, K. Y. (2000).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LePoer, B. L. (1991). Historical setting.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June 10, 2008 from http://lcweb2.loc.gov/ cgi-bin/query/r?frd/cstdy:@field(DOCID?sg0033).
Long, M. H. (1996).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W. C. Ritchie & T. K. Bhatia (Eds.),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413–468).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Long, M. H., Inagaki, S., & Ortega, L. (1998). The role of implicit negative feedback in SLA: Models and recasts in Japanese and Spanish.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2(3), 357–371.
Lui, T. Y. (2006). Speech by RADM (NS) Lui Tuck Yew,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t the launch of the 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on Tuesday, 25 July 2006, 11.00 am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Accessed May 29, 2008 from http://stars.nhb.gov.sg/stars/ public/.
Mackey, A., & Oliver, R. (2002). Interactional feedback and children’s L2 development. System, 30, 459–477.
Marinova-Todd, S., Marshall, D. B., & Snow, C. E. (2000). Three misconceptions about age and L2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34(1), 9–34.
Martin, M. O., Mullis, I. V. S., Gonzalez, E. J., Gregory, K. D., Smith, T. A., Chrostowski, S. J., et al. (1999). TIMSS 1999 international science report: Findings from IEA’s repeat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at the eighth grade.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Accessed October 1, 2001 from http://timss.bc.edu/timss 1999i/ publications.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 Changes to primary education.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cessed October 6, 2006 from http://www.moe.gov. sg/corporate/eduoverview/Primary_changesToPri. 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 Refining how we deliver ability-driven education. Accessed December 6, 2006 from http://www.moe.gov.sg/press/2006/pr20060928. htm.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a). Changes affecting special/ express courses. Accessed September 21, 2007 from http://www.moe.gov.sg/corporate/eduoverview/Sec_ changes.htm.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b). Preparing students for a global future: Enhancing language learning.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07 from http://www.moe.gov.sg/ press/2007/pr20070307.htm.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c). Programmes offered. Accessed September 21, 2007 from http://www. moe. gov.sg/esp/schadm/sec1/Progs_Offered.htm.
Mullis, I. V. S., Martin, M. O., Gonzalez, E. J., Gregory, K. D., Garden, R. A., O’Connor, K. M., et al. (1999). TIMSS 1999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report: Findings from IEA’s repeat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at the eighth grade.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Accessed October 1, 2001 from http://timss.bc.edu/timss 1999i/ publications.html.
Mullis, I. V. S., Martin, M. O., Gonzalez, E. J., & Kennedy, A. M. (2003). PIRLS 2001 international report: IEA’s study of reading literacy achievement in primary schools. Chestnut Hill, MA: Boston College.
Newman, J. (1988). Singapore’s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9(5), 437–448.
Oyama, S. (1976/1982).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 nonnative phonological system. In S. Krashen, R. C. Scarcella, & M. H. Long (Eds.), Child-adult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0–38).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Pakir, A. (1993). Two tongue tied: B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4(1&2), 73–90.
Pakir, A. (1997). Education and 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English in Singapore. In J. Tan, S. Gopinathan, & W. K. Ho (Ed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book of readings (pp. 55–72).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Pakir, A. (1999). English in Singapore: The codification of competing norms. In S. Gopinathan, A. Pakir, W. K. Ho, & V. Saravanan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p. 65–84).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akir, A. (2000). Singapore. In W. K. Ho & R. Y. L. Wong (Eds.), 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mpact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next decade (pp. 259–284). Singapore: Times Media.
Pica, T. (1987).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classroom. Applied Linguistics, 8(1), 3–21.
Pica, T., Young, R., & Doughty, C. (1987). The impact of interaction on comprehension. TESOL Quarterly, 21(4), 737–758.
Pinker, S.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Riney, T. (1998). Toward more homogeneous bilingualisms: Shift phenomena in Singapore. Multilingua, 17(1), 1–23.
Rubdy, R. (2001). Creative destruction: Singapore’s 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World Englishes, 20(3), 341–355.
Saravanan, V. (1999).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the Tamil–English community. In S. Gopinathan, A. Pakir, W. K. Ho, & V. Saravanan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pp. 155–178).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Saravanan, V., Lakshmi, S., & Caleon, I. (2007). Attitudes towards literary Tamil and standard spoken Tamil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0(1), 58–79.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Singapore population. Singapore Government. Accessed May 17, 2002 from http://www.singstat.gov.sg/keystats/ c2000/handbook.pdf.
Singapore Government. (1965). Singapore year book 1965.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ingapore Government. (1966).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Annual report (pp. 10). 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Snow, C. E. (1990). Rationales for nativ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language minority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esearch. In A. Padilla, H. Fairchild, & C. Valadez (Eds.), Bilingual education: Issues and strategies (pp. 60–74).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oud, C., & Wee, L. (2007). Consuming identit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Singaporean late modernity. Language Policy, 6(2), 253–277.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S. M. Gass & C. G.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235–253).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Swain, M. (1995).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G. Cook & B. Siedlhofer (Eds.), Principle and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Studies in honour of H.G. Widdowson (pp. 125– 14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wain, M., & Lapkin, S. (1982). Evaluating bilingual education: A Canadian case study.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Tan, J. (1997a). Education and colonial transition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Comparative Education, 33, 303–312.
Tan, L. Y. (1997b). Communal riots of 1964. National Library Board. Accessed June 10, 2008 from http:// infopedia.nl.sg/articles/SIP_45_2005-01-06.html.
Tauli, V. (1968).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Uppsala, Sweden:
Almqvist & Wiksells.
Vigil, N. A., & Oller, J. W. (1976). Rule fossilization: A tentative model. Language Learning, 26(2), 281–295.
Wee, L. (2002). 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 and bilingualism in Singapore: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 Acta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pp. 1107–1120). Vigo, Spain: University of Vigo.
Xu, D., Chew, C. H., & Chen, S. (1999).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In S. Gopinathan, A. Pakir, W. K. Ho, & V. Saravanan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pp. 133– 154).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Yip, J. S. K., Eng, S. P., & Yap, J. Y. C. (1990). 25 year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J. S. K. Yip & W. K. Sim (Eds.),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excellence: 25 years of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pp. 1–25). Singapore: Longman.
Yip, J. S. K., Eng, S. P., & Yap, J. Y. C. (1997). 25 year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J. Tan, S. Gopinathan, & W. K. Ho (Ed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book of readings (pp. 3–32). New York: Prentice Hall.